MEMO在4月初舉辦了「以愛為名」教育反思分享會,邀請了三位嘉賓細談家庭、學校中各種「為你好」的管教。嘉賓之一的海星校長、白鷺老師在2007年創辦鄉師自然學校,身體力行推廣另類教育,便在當日和我們談到自然學校裡的師生關係。
M=MEMO;海=海星校長;白=白鷺老師
M:聽說自然學校是一間沒有校規的學校?
海:自然學校沒有名義上的校規,但就有師生共同遵守的「生活公約」,譬如學校重視自然健康,所以校內所有人需要吃素、不可隨便吃包裝零食。全校師生每周會召開「生活會議」,師生一起討論修訂公約,譬如不可吃蝦條薯片,那可否吃有機朱古力?衣著方面我們有原則,就是簡樸、自然、耐污,但不會執著裙的長度、頭髮的長度等等。
M:最近的「生活會議」有哪些有趣討論?
白:有學生早前提議在學校養羊,然後同學仔逐一列出養羊的好處和壞處,想養的同學便學習怎樣說服其他同學。有同學贊成,說因為校內的貓整天躲起來,不易接觸,但羊很可愛也不會躲藏。有同學反對,說害怕羊吃掉後花園的菜,一位小三同學也不贊成養羊,說因為羊仔會死,面對死亡會令他很難過。
M:老師作為成年人,通常都會想「幫」小朋友快一些「解決問題」,為何要花大量時間討論?
海:我們相信公民社會就是這樣運作的,所以希望讓同學們有更多空間去對話、去決定。譬如早幾年很流行玩BS卡(卡牌對戰遊戲),有學生提議准許帶回學校玩。作為自校老師,我們當然希望學生更多接觸人和自然,但也讓學生們互相討論。結果頗意外,不少同學最終不支持,證明學生也不一定永遠站在學生一邊。
當然,學校也有一些堅守的原則,譬如不可食肉,但有些約定,如不可吃零食,也是可以商議的。有同學會嘗試指出有機朱古力比較健康,但老師便提到零食有很多即棄包裝。除了生活會議,我們還有「生活教育法庭」,學生和老師都有權可以寫「狀紙」。
M:「生活教育法庭」有過什麼案例?
海:有一次老師在雜物室看到幾隻老鼠BB,所以帶來一隻學校的貓滅鼠,結果被學生見證過程,覺得太殘忍,於是認為老師做得不夠好。生活教育法庭每日開庭,設有老師法官、學生法官,也有由數名學生組成的「陪審團」。庭上便有討論到如果老師當初不介入,貓是否就不會吃掉老鼠。最終結論是兩邊也有道理,但老師在情感上傷害了同學,所以老師也有道歉,並決定日後再有同類情況時,應該一同商量做法。
M:自然學校的同學升上主流中學後,會否很難適應?
海:其實一般主流學校的學生,很多都沒玩夠、不能定下來學習,自小被管大的學生,自律能力反而不高,但我們自然學校的學生,反而容易產生自律。我們都在和小朋友在學習「非暴力溝通」,不要將「對/不對」掛在嘴邊。我自己有時也會生起那種「長輩就是正確」的想法,但我會嘗試提高自己的覺察力,有時會「hang機」,有時會暴走,這是一份持續的功課,不是一兩堂便能學懂。
白:我有兩個囡囡,都在自然學校長大,大囡升中時,我讓她自由選擇要不要去主流學校,然後她便去主流學校試下,結果成績非常好,也是老師眼中的優異生,然後讀了兩年半後決定退學,說主流學校對她的期望,其實就只有讀書一事。
M=MEMO;洪=洪曉嫻Kitty
M:你在種植班接觸過不少親子檔,你對現在的親子關係觀察是怎樣的?
洪:見過有小朋友初試落田,接觸泥濘時有些敏感、害怕,其實也很正常,結果她的父母立即十分焦急:「點解人哋做到,你會做唔到㗎,好小事咋嘛 」,結果家長和小朋友的情緒一起「爆炸」。傳統教育常常否定和壓抑小朋友的情緒,但其實情感很需要被重視。鼓勵小朋友表達情緒,並接受他們的情緒,對小朋友來說是很大的empowerment(充權)。
M:你和囡囡又是怎樣相處的?
洪:成為媽媽之後,我第一次感受到一個人獲得「絕對權力」的感覺,你可以絕對主宰自己的小朋友,去決定他做什麼或不做什麼。作為一個認為應在日常中實踐民主的人,我時刻提醒自己——當我擁有這麼絕對的權力時,應該怎麼使用。
相處之中,我會明確指出「你是獨立的,我也是獨立的」,我們之間要建立一些邊界。有一次,我的囡囡玩完了我整枝全新的護髮素,我問她為何這樣做,原來她是想做實驗,研究護髮素能否製造出「鬼口水」。但我也有要求她賠錢,賠錢的行為是為了說明邊界,有邊界才能確立大家的主體性,然後學懂互相尊重。
有朋友說,她的兒子聲稱以後不要再睡覺,嚇得我朋友連忙阻止,但我的想法是「好啊,這是很好的實驗」,然後我便鼓勵朋友和她兒子一起做實驗,看看一個人到底可以撐多少天不睡覺, 寫或者畫一份report,但如果中途一睡著的話,實驗便即時結束了。和小朋友相處就是要be creative,除了一下子就說不可以,我們有沒有其他有趣的應對方法呢?
M:想聽多一些你和女兒是怎樣劃邊界的?
洪:從小到大,我和她都是「壁壘分明」的,她的東西就是她的,如果我要用她的東西,我要問她借的,反之亦然。這確立了一個人是獨立個體,那怕她是一個小朋友。
我在女兒小時候從不讓她吃薯片、珍寶珠等垃圾食物,但她長大到4、5歲時,始終不是在深山,便一定會接觸到這些零食。我發現,她會瞞著我、偷偷要求其他人買給她吃。有一次,她悄悄收起了一顆kinder出奇蛋,但忘記吃掉,怕被我罵而嚇得哇一聲大哭。
這件事令我當頭棒喝,原來你不准她做,她怎麼都會找方法做。後來,我和她一起訂了「零食券」方案,每個月可以用一張,讓她喜歡買什麼就買什麼。得不到的,是最誘惑的,得到了之後,家中放一排朱古力她也完全不想吃,反而問「幾時可以食提子?」
我要尊重她是一名獨立的人,不可以強加自己想法在她身上。譬如有一天她說「媽媽我想化妝」,我初初有些錯愕,但也用了一些做手工的礦物為她拌成化妝品。她試了兩日化妝,結果到第三日,我早上提她要早點起床化妝,結果她說早起很煩,還是不化了(笑)。這個互動是一種疏導,我不是視她為一個心智不成熟、需要我加以管教的人,而是一個有能力溝通的人。
M=MEMO;L=Louie;海=鄉師自然學校校長海星;洪=生活Kids Club成員洪曉嫻
M:可否分享下你過往與校方溝通的經歷?
L:學校每年都會循例舉行一次「輕輕鬆鬆話XX(校名)」的活動,每班派2名代表向校方反映對學校的意見,譬如希望開放後門,讓學生回校無須兜路,表面像是有效的諮詢大會,實際上聽過無數次回應都是「我們在跟進、我們會考慮」, 感覺很正面,但年年答覆都一樣,最後也是不了了之。
我在中五時參選學生會,當時花了半年構思一個有效的諮詢架構,設有直選和不同功能界別,讓學生、教師、家長、校友代表有平衡的參與。本來以為可以再和老師協商如何調整方案,結果翌日便被老師「照肺」,批評我們「造反、與學生會職能背道而馳」。那名老師其實一向比較開明,我相信他也承受了高層壓力。我很不喜歡這一點,高層不會直接罵我們,但會透過班主任或其他老師向我們施壓。
我們參選時也提出,希望籌辦更多職涯規劃的講座,但老師也反對,說不是學生會職能,學校自會安排,但我心想「正正就係同學唔滿意學校安排,我哋先提出來嘛」。老師不斷要求我們刪減政綱,結果我們與另一內閣最不同的賣點都被刪走了,感覺校方只想學生會「hea做」。
學校以前的排名不算太差,也有band 2頭,讀書差一些,但在不少體藝比賽中奪獎,但後來換了校長和副校長,副校長覺得「你班人又唔讀書,又玩埋咁多嘢」,於是削減課外活動來催谷成績,結果令到同學讀書差、課外活動亦差,成功在數年間令我們跌到band 3尾。
洪:我一直有執教中學的創意寫作班,但因為我染了粉紅色頭髮,曾經有老師建議我戴帽遮一遮,最後我綁了一個更誇張的粉紅色蝴蝶結,去遮住那一束頭髮。哪怕我已經不是一個正式的教員,我還要面對這些⋯⋯很多年前便以為不再需要面對的髮飾儀容規限。
關於中學,我還有三點觀察,第一是近兩年,每班都有學生有自殺傾向,不同學校都出現。第二,我發現如今中學生筆下沒題材,沒有有趣的事發生,沒有值得書寫的地方,拍拖也不拍,生活都很枯燥,其實令人很傷心。
第三,我最近參觀中學教育展,震驚地發現正向教育被扭曲得很可怕。正向教育本來是鼓勵教師要正向地擁抱學生的不同,卻變成要求學生只能有正面情緒,譬如展覽說「氣餒」是負面的、要剔除的,但其實應該是擁抱「氣餒」、理解「氣餒」,才能轉化為正面情緒,我很擔心中學生現時面對的情緒壓抑。
海:我以前也曾在一般村校教書,身為有另類觀點的人都是艱難的。當時村校計劃安裝冷氣,我作為體育老師自然想反對,因為學生跑跳之後吹冷氣很容易病,但我是少數所以無法阻止。作為學生,大概是一個無權力者,我很明白在制度內爭取改變的困難。其實很多主流學校老師都很好、非常關心學生,但一觸碰到學校體制問題,便很難改變,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跳出來,開自己的學校。
M:香港有沒有空間去設立自然學校的「中學版」?
海:不是不可能,只是比較艱難。即使開不了自然中學,但我覺得學習不一定要局限在中學之內,學校之外的天空非常廣闊。其實我們有在進行中學版的實驗課程,招收15歲或以上已完成強制教育的青少年。
L:主流體制在扼殺學生的另類機會,只會要求讀書,我在學校也有常常邀請同學參與校外活動,譬如做義工、拓展自己興趣,死讀書也不代表能一帆風順。不過,如果讓我重來一次,我其實仍然會選擇入讀官校。那段經歷當時給我很大壓力,但當我捱過之後,我現在面對DSE也不覺得有壓力(笑)。如果我當初入讀自然學校,我便體會不到官校的這些問題了。
M:學校不斷要求學生讀書,你覺得這種教育當中有沒有「愛」?
L:我不能否認教育的出發點本身是有愛的,但在執行時,高層或前線也好,仗著自己有愛,覺得自己一定是對的,而否定學生想法,忽略了最終的教育效果。
早兩年疫情嚴重時,教育局指引不準學生在中午後留校,老師會準時趕走學生,我的一位同學有抑鬱症,某次放學後伏在桌上哭泣,朋友和我在旁安撫,結果副校長堅持趕走我們,最後將那位同學帶到圖書館,任由他自己哭。另一次,當那名同學有情緒時,副校長便帶他在校內到處走走,說「其實個世界冇你想像中咁黑㗎咋,都好美好㗎」,結果那名同學情緒更差,只覺得「原來我係一個怪胎」。如果校方永遠覺得自己正確,其實很恐佈。
聽眾A:同學分享他在學校遇到的狀況,其實我們在長者中心也一樣。我們長者中心每年都有諮詢大會,然後那些管理人員的答案也一模一樣:「我們在跟進」。(全場大笑)。對同學來說,長輩常常將「為你好」掛在嘴邊,但對我們長者來說,很多子女也是翻炒這三個字:「為你好」,於是疫情時不准我們外出、不准我們堂食,仍是那一句「為你好」。我的老友記形容,這其實是虐老。
聽眾B:我是小學老師,對香港整個教育制度感到費解,好難改變,其他老師會教我一定要惡、要令學生怕自己,但我沒有,於是被學生「恰」,上我的堂便會很嘈吵,但上其他堂很安靜。我仍有一直在反思,嘗試尊重他們是獨立的個體,而不是spoon-feed他們。
聽眾C:我是特殊學校老師,接觸自閉症和輕智學生。其中一名小二學生語言能力有限,有自閉症和輕度智障,常常拒絕進入課室。因為學校始終想學生在未來出社會後懂得守規範、聽指令,那當他拒絕入課室時,我們便會和他倒數20秒之類,不然就抱進去。他也很容易被身邊小朋友的情緒所牽動,會發脾氣甚至向老師拳打腳踢、沖出課室。我在想,小朋友不fit in主流學校所以去了特殊學校,但去了特校,他也不fit in,他也做不到安坐、聽指令。
海:其實一定要入課室安靜也是一種主流想法。我們也有學生不肯入課室,但如果他的需要不被滿足的話,其實入了課室也無用。因為他不懂說出來,便用這種(不入課室)方式表達感受。不論主流或非主流老師在能力上都應該敏感些,但大學院校訓練老師時只教管理,也比較少教老師如何處理學生情緒,所以老師不懂其實也很正常。
我現在也常告訴老師們,不要被一個安靜的課堂欺騙了,以為很有秩序,其實學生沒有在學習,反而是有點嘈的課堂才是正在學習。我們一直希望老師不依賴獎勵、不依賴懲罰,去處理課堂秩序,而是透過「非暴力溝通」,這是值得嘗試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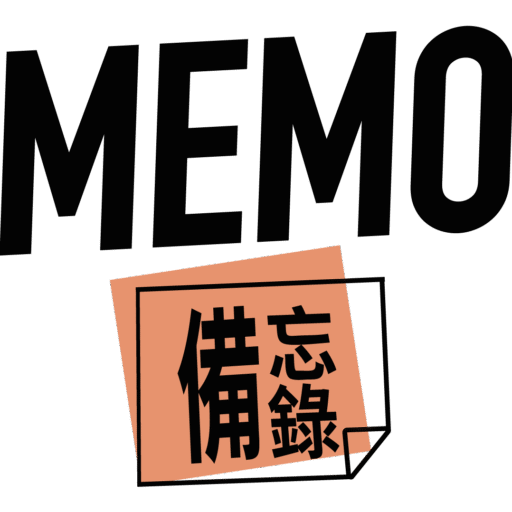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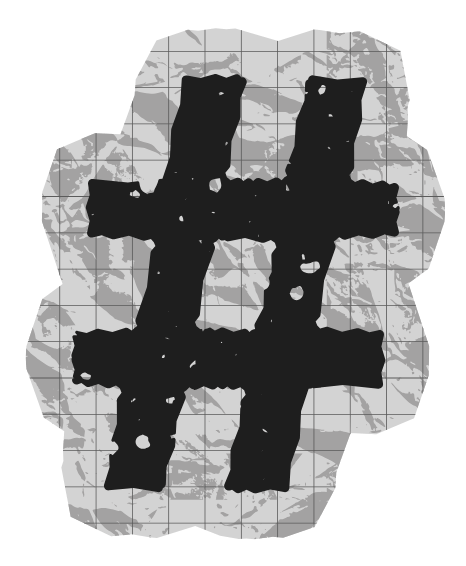

•-Instagram-相片與影片-Google-Chrome-30_06_2025-23_02_23.png)
•-Instagram-相片與影片-Google-Chrome-30_06_2025-22_28_29.png)
•-Instagram-相片與影片-Google-Chrome-30_06_2025-22_28_38.png)
•-Instagram-相片與影片-Google-Chrome-30_06_2025-22_28_44.png)
發佈留言